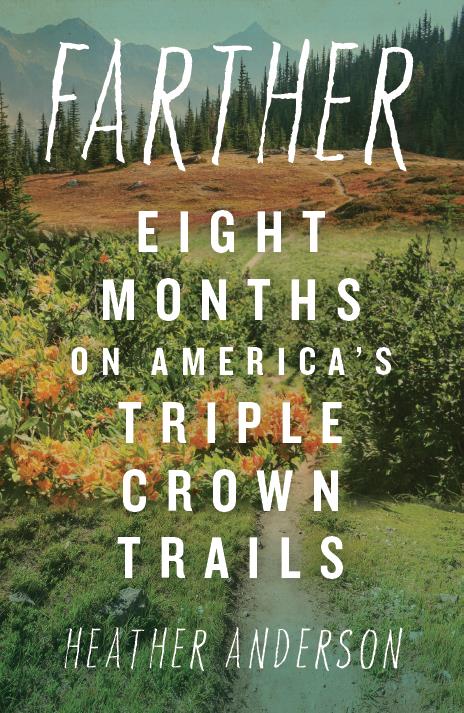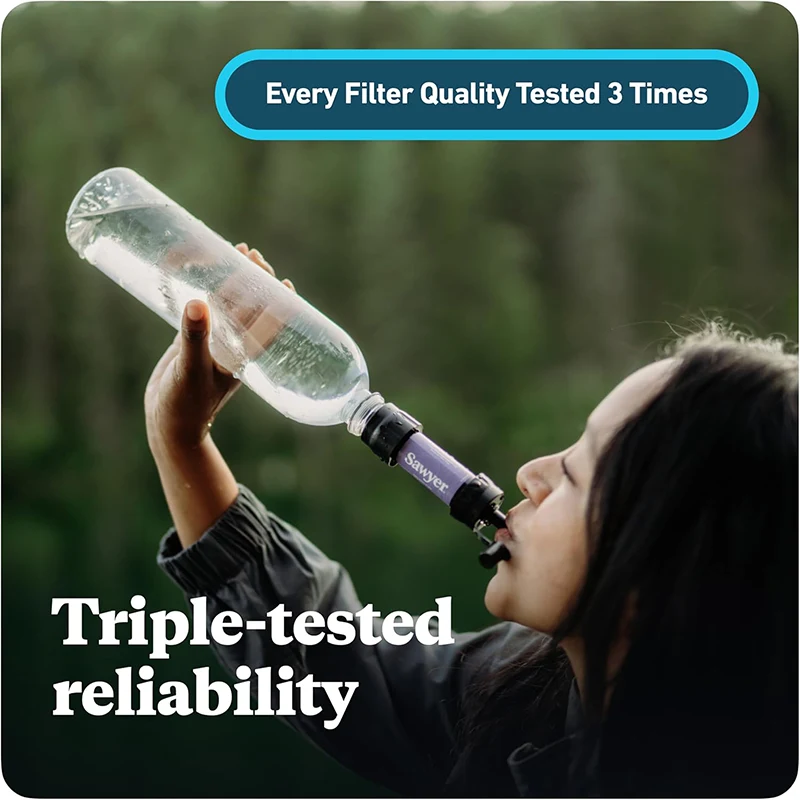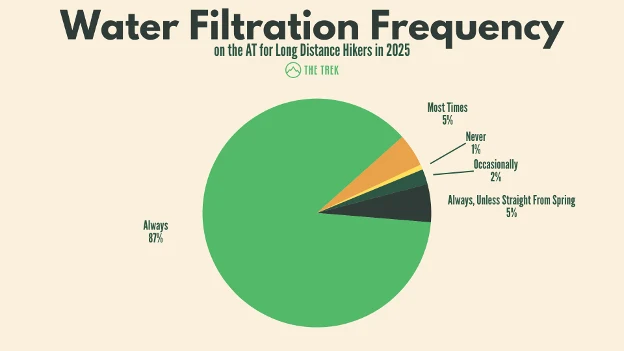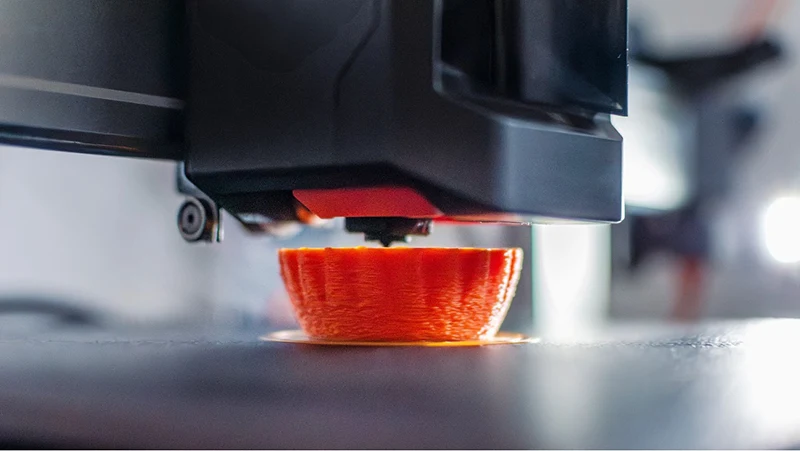户外活动中的性别自由
户外活动中的性别自由

户外活动中的性别自由
YouTube video highlight
On the trails around Blacksburg, I found peace and freedom from a gendered society.
Read more about the project我决定徒步穿越阿巴拉契亚步道,因为我想要逃离。2021 年 9 月,也就是我大四那年,我正成为我所希望的一切的对立面。我避免写任何东西,在一段长达两年半的恋情接近尾声时,我还记得自己当时的想法:"我宁愿在这段恋情中,也不愿意离开:我宁愿这样,也不愿面对我自己,几乎每晚都昏睡过去。一觉醒来,我的作业已经完成,但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交上去的。我还会在剧烈的颤抖中醒来,感觉世界要撕裂了(临床上称为 "末日来临感"),感觉自己要发作了,这些都是酒精戒断患者的常见症状。戒酒?我才 21 岁,我到底在极力逃避什么?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,答案很简单:我自己。

有很多次,我知道自己需要改变。在一屋子忧心忡忡的朋友面前,抓着打不开的酒瓶把手。在前男友告诉我他不相信同性恋,变性人不应该存在后,我在车里泣不成声。翻开一页页空空如也的笔记本,上面只有泪痕。我唯一能找到的安宁就是逃到布莱克斯堡周围的阿巴拉契亚小径,在那里,我最担心的是找到回到小径头的路,以及安全地爬下岩壁。如果我还想继续徒步旅行,就不能喝酒。
这条山路教会我尊重自己的身体--因为如果我不尊重自己的身体,就很难继续前行。
在山路上,如果没有手机服务,我就无法听到厌恶变性人的评论,而我的身体能带我俯瞰令人难以置信的美景,这让我的性别焦虑症得到了缓解。在我独自远足和背包旅行的过程中,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既不像女人,也不像男人。我介于两者之间,和周围的自然世界一样自由。我无法融入性别社会。在山路上,我对每一张要求我勾选男性或女性的表格都犹豫不决。每走进一间浴室,我都会考虑再三。我害怕用代词介绍自己;我担心自己不够 "他们/她们"(they/them),不够 "她/她"(she/her)(straight)。我想尖叫。于是我就这么做了--我走到小路上(在确认周围没人后)尖叫。我想上厕所就上厕所,想挖洞就挖洞,感觉自己是个粗犷的户外人。
在户外,我会忘记一切形式、卫生间和代词,只为活着而欣喜。我可以做我自己。我是谁一个诗人,一个恶棍,一个人类。山不在乎我也不在乎
一天下午,当我坐在龙牙山山顶看日落时,我突然意识到,如果我不开始接受自己,我可能会在认识真正的自己之前就死去。于是,我离开了这段关系。在那之前,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。我知道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
毕业后,我找到了一份工作,这份工作也给我带来了和恋爱时一样的束缚感。在那里工作的头六个月,我就遭到了某人的性骚扰,而且我从未觉得自己可以谈论任何有关我的性别或性取向的事情。
我又回到了壁橱里,只不过这一次,我又多了一份恐惧,那就是我被困在了一个老男人们认为很有吸引力--而且经常让我知道--的同性女性身体里。
这不是我第一次遭遇性骚扰。16 岁那年,我在一家餐厅工作的两年里,几乎每晚都会遭到性骚扰,餐厅里三四十岁的男人会抓住我的臀部,把我束缚起来让别人亲吻。我以为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会有所不同。我错了。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老板,他告诉我:这种事情还会发生。 于是我辞职了。我开始敲定我最大的逃离计划:徒步穿越阿巴拉契亚步道。
与此同时,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越野跑中。我一直喜欢探险跑。上高中时,放学后跑上三四个小时,意味着我可以探索高山,闯入玉米地,沿着废弃的火车顶跑。在我的身体经常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被用来对付我的时候,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
就这样,在新工作遭遇性骚扰三个月后,我发现自己站在了 50 公里赛的起跑线上。

这一次,通过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超级马拉松俱乐部,跑步给我带来了一个由新朋友组成的支持系统,也给我带来了一如既往的自由。我告诉自己,我是在用跑步来准备参加 AT。然而,跑步成了我的新嗜好。我已经训练过度。
在超马过程中,我能感觉到我的膝盖内侧韧带像橡皮筋一样绷得紧紧的。我感到非常疼痛。但我不想让它停下来。我跑得更卖力了。我很生气。我的每一脚都踩在地上,我感到沮丧,尽管我有资格胜任这份工作,尽管我已经从一段有毒的关系中解脱出来,尽管我开始接受自己的非二元身份--但这并不重要。面对那些未经我同意就将我的身体性化的人,我仍然无能为力。我甚至对自己是个女人都没有共鸣,而其他人却在利用我的女性特征来对付我。我不想待在自己的身体里。我在身体里无能为力。除了我可能对它造成的伤害之外,我无能为力,在那些时刻,我觉得我的身体活该。我觉得我活该
赛后,我几乎无法行走。回到家后,我无法进食、喝水或排便。我(真的)爬到了床上。当我醒来时,我的左腿抬不起来,臀部灼痛难忍。我本该在两个月内徒步走完阿巴拉契亚步道。我做了什么?

一夜之间,我从未来的徒步旅行者和超级马拉松运动员变成了受伤、失业、住在朋友沙发上的流浪汉。哎呀。生活总是让我惊讶,它能如此迅速地改变我的自我认知。我决定将我的上瘾性格转化为强烈的自我保健。这一次,我全身心地投入到物理治疗中。理疗师说的任何话都是我的个人戒律。在我痴迷跑步的过程中,我的臀部已经错位,现在我要努力让它们恢复水平。理疗师要求我平躺,减少走路,每天做三次以上的拉伸运动。起初,这似乎很容易做到--但如果试着坚持两个多月,就会变得很困难。有很多天,我都很难不对自己的身体--总的来说,对自己--再次感到沮丧。我把自己搞得一团糟。这都是我的错,我甚至可能无法踏上我计划了一年的旅程,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场长达六小时的比赛。
每当这些念头开始悄然袭来,我就意识到担心未来毫无意义,因为我还没到那一步。我让自己感受到内疚和遗憾,然后温和地告诉自己是时候向前看了。我会吃点零食(通常我只是饿了)、喝点水,然后把挫败感转化为弹吉他、画水彩画或写诗,让自己回到当下。当消极情绪渗透进来时,我发现最好先找一些事情来帮助我的身体,然后再做一些事情来帮助我的心灵。用莎士比亚的话说,没有什么东西是好的或坏的,是思想让它变成这样的。 在一次独自徒步旅行中,我曾向一位徒步旅行者请教,他说:"有时,当事情真的很艰难时,你只需要坐下来呼吸一分钟。在恢复的那两个月里,我做了很多呼吸。

我每天都做伸展运动,尽力庆祝每一个小小的胜利。我抱着这样的心态:每天,我的身体都在一点一点地康复。你允许自己头脑中出现的负面想法越多,你赋予自己的力量就越大--你可以从我在超级马拉松比赛中的思维过程中看到这一点。如果我对自己的身体和未来的目标有更多的关注,也许我就会停下来,更多地去照顾自己。消极只会滋生不幸。无论如何,这段恢复期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,让我更加乐观,更加善待自己。毕竟只有我一个人住在我的脑海里,所以我不妨把它变成一个美好的地方。
我尽力保持积极的心态,因为我取得了一些小的胜利,比如躺下时可以伸直腿,可以完全直立,可以迈开步子,可以再次行走--然后,可以再次行走一英里以上。我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深的了解和尊重。自我憎恨可能会推动我走完 32 英里,但它不会帮助我走完 2000 英里。时至今日,在 73 天的时间里,我没有错过任何一次重复的拉伸运动。我计划继续在山路上锻炼。

现在,我把 4 月 19 日的出发日期看作不仅是一次逃离,更是一次自我接纳之旅。一路上,我将为 "Venture Out 项目"筹款,这是一个非营利组织,专门为同性恋和变性人提供背包旅行服务,让其他人也能在大自然中找到与我一样的释放和力量。我希望我的自我接纳之旅能够帮助其他人迈出自己的第一步。在布莱克斯堡周围的小径上,我找到了平静,从性别社会中获得了自由。在一次超级马拉松比赛后,我找到了自我的力量和对身体的尊重。更重要的是,我在自己的皮肤上找到了一个家,并找到了时间来治愈我的心灵和身体之间的联系。如果我在准备越野赛的过程中发现了所有这些自我发现,那么我迫不及待地想在缅因州找到自己。
户外活动中的性别自由


我决定徒步穿越阿巴拉契亚步道,因为我想要逃离。2021 年 9 月,也就是我大四那年,我正成为我所希望的一切的对立面。我避免写任何东西,在一段长达两年半的恋情接近尾声时,我还记得自己当时的想法:"我宁愿在这段恋情中,也不愿意离开:我宁愿这样,也不愿面对我自己,几乎每晚都昏睡过去。一觉醒来,我的作业已经完成,但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交上去的。我还会在剧烈的颤抖中醒来,感觉世界要撕裂了(临床上称为 "末日来临感"),感觉自己要发作了,这些都是酒精戒断患者的常见症状。戒酒?我才 21 岁,我到底在极力逃避什么?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,答案很简单:我自己。

有很多次,我知道自己需要改变。在一屋子忧心忡忡的朋友面前,抓着打不开的酒瓶把手。在前男友告诉我他不相信同性恋,变性人不应该存在后,我在车里泣不成声。翻开一页页空空如也的笔记本,上面只有泪痕。我唯一能找到的安宁就是逃到布莱克斯堡周围的阿巴拉契亚小径,在那里,我最担心的是找到回到小径头的路,以及安全地爬下岩壁。如果我还想继续徒步旅行,就不能喝酒。
这条山路教会我尊重自己的身体--因为如果我不尊重自己的身体,就很难继续前行。
在山路上,如果没有手机服务,我就无法听到厌恶变性人的评论,而我的身体能带我俯瞰令人难以置信的美景,这让我的性别焦虑症得到了缓解。在我独自远足和背包旅行的过程中,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既不像女人,也不像男人。我介于两者之间,和周围的自然世界一样自由。我无法融入性别社会。在山路上,我对每一张要求我勾选男性或女性的表格都犹豫不决。每走进一间浴室,我都会考虑再三。我害怕用代词介绍自己;我担心自己不够 "他们/她们"(they/them),不够 "她/她"(she/her)(straight)。我想尖叫。于是我就这么做了--我走到小路上(在确认周围没人后)尖叫。我想上厕所就上厕所,想挖洞就挖洞,感觉自己是个粗犷的户外人。
在户外,我会忘记一切形式、卫生间和代词,只为活着而欣喜。我可以做我自己。我是谁一个诗人,一个恶棍,一个人类。山不在乎我也不在乎
一天下午,当我坐在龙牙山山顶看日落时,我突然意识到,如果我不开始接受自己,我可能会在认识真正的自己之前就死去。于是,我离开了这段关系。在那之前,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。我知道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
毕业后,我找到了一份工作,这份工作也给我带来了和恋爱时一样的束缚感。在那里工作的头六个月,我就遭到了某人的性骚扰,而且我从未觉得自己可以谈论任何有关我的性别或性取向的事情。
我又回到了壁橱里,只不过这一次,我又多了一份恐惧,那就是我被困在了一个老男人们认为很有吸引力--而且经常让我知道--的同性女性身体里。
这不是我第一次遭遇性骚扰。16 岁那年,我在一家餐厅工作的两年里,几乎每晚都会遭到性骚扰,餐厅里三四十岁的男人会抓住我的臀部,把我束缚起来让别人亲吻。我以为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会有所不同。我错了。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老板,他告诉我:这种事情还会发生。 于是我辞职了。我开始敲定我最大的逃离计划:徒步穿越阿巴拉契亚步道。
与此同时,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越野跑中。我一直喜欢探险跑。上高中时,放学后跑上三四个小时,意味着我可以探索高山,闯入玉米地,沿着废弃的火车顶跑。在我的身体经常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被用来对付我的时候,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
就这样,在新工作遭遇性骚扰三个月后,我发现自己站在了 50 公里赛的起跑线上。

这一次,通过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超级马拉松俱乐部,跑步给我带来了一个由新朋友组成的支持系统,也给我带来了一如既往的自由。我告诉自己,我是在用跑步来准备参加 AT。然而,跑步成了我的新嗜好。我已经训练过度。
在超马过程中,我能感觉到我的膝盖内侧韧带像橡皮筋一样绷得紧紧的。我感到非常疼痛。但我不想让它停下来。我跑得更卖力了。我很生气。我的每一脚都踩在地上,我感到沮丧,尽管我有资格胜任这份工作,尽管我已经从一段有毒的关系中解脱出来,尽管我开始接受自己的非二元身份--但这并不重要。面对那些未经我同意就将我的身体性化的人,我仍然无能为力。我甚至对自己是个女人都没有共鸣,而其他人却在利用我的女性特征来对付我。我不想待在自己的身体里。我在身体里无能为力。除了我可能对它造成的伤害之外,我无能为力,在那些时刻,我觉得我的身体活该。我觉得我活该
赛后,我几乎无法行走。回到家后,我无法进食、喝水或排便。我(真的)爬到了床上。当我醒来时,我的左腿抬不起来,臀部灼痛难忍。我本该在两个月内徒步走完阿巴拉契亚步道。我做了什么?

一夜之间,我从未来的徒步旅行者和超级马拉松运动员变成了受伤、失业、住在朋友沙发上的流浪汉。哎呀。生活总是让我惊讶,它能如此迅速地改变我的自我认知。我决定将我的上瘾性格转化为强烈的自我保健。这一次,我全身心地投入到物理治疗中。理疗师说的任何话都是我的个人戒律。在我痴迷跑步的过程中,我的臀部已经错位,现在我要努力让它们恢复水平。理疗师要求我平躺,减少走路,每天做三次以上的拉伸运动。起初,这似乎很容易做到--但如果试着坚持两个多月,就会变得很困难。有很多天,我都很难不对自己的身体--总的来说,对自己--再次感到沮丧。我把自己搞得一团糟。这都是我的错,我甚至可能无法踏上我计划了一年的旅程,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场长达六小时的比赛。
每当这些念头开始悄然袭来,我就意识到担心未来毫无意义,因为我还没到那一步。我让自己感受到内疚和遗憾,然后温和地告诉自己是时候向前看了。我会吃点零食(通常我只是饿了)、喝点水,然后把挫败感转化为弹吉他、画水彩画或写诗,让自己回到当下。当消极情绪渗透进来时,我发现最好先找一些事情来帮助我的身体,然后再做一些事情来帮助我的心灵。用莎士比亚的话说,没有什么东西是好的或坏的,是思想让它变成这样的。 在一次独自徒步旅行中,我曾向一位徒步旅行者请教,他说:"有时,当事情真的很艰难时,你只需要坐下来呼吸一分钟。在恢复的那两个月里,我做了很多呼吸。

我每天都做伸展运动,尽力庆祝每一个小小的胜利。我抱着这样的心态:每天,我的身体都在一点一点地康复。你允许自己头脑中出现的负面想法越多,你赋予自己的力量就越大--你可以从我在超级马拉松比赛中的思维过程中看到这一点。如果我对自己的身体和未来的目标有更多的关注,也许我就会停下来,更多地去照顾自己。消极只会滋生不幸。无论如何,这段恢复期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,让我更加乐观,更加善待自己。毕竟只有我一个人住在我的脑海里,所以我不妨把它变成一个美好的地方。
我尽力保持积极的心态,因为我取得了一些小的胜利,比如躺下时可以伸直腿,可以完全直立,可以迈开步子,可以再次行走--然后,可以再次行走一英里以上。我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深的了解和尊重。自我憎恨可能会推动我走完 32 英里,但它不会帮助我走完 2000 英里。时至今日,在 73 天的时间里,我没有错过任何一次重复的拉伸运动。我计划继续在山路上锻炼。

现在,我把 4 月 19 日的出发日期看作不仅是一次逃离,更是一次自我接纳之旅。一路上,我将为 "Venture Out 项目"筹款,这是一个非营利组织,专门为同性恋和变性人提供背包旅行服务,让其他人也能在大自然中找到与我一样的释放和力量。我希望我的自我接纳之旅能够帮助其他人迈出自己的第一步。在布莱克斯堡周围的小径上,我找到了平静,从性别社会中获得了自由。在一次超级马拉松比赛后,我找到了自我的力量和对身体的尊重。更重要的是,我在自己的皮肤上找到了一个家,并找到了时间来治愈我的心灵和身体之间的联系。如果我在准备越野赛的过程中发现了所有这些自我发现,那么我迫不及待地想在缅因州找到自己。
户外活动中的性别自由


我决定徒步穿越阿巴拉契亚步道,因为我想要逃离。2021 年 9 月,也就是我大四那年,我正成为我所希望的一切的对立面。我避免写任何东西,在一段长达两年半的恋情接近尾声时,我还记得自己当时的想法:"我宁愿在这段恋情中,也不愿意离开:我宁愿这样,也不愿面对我自己,几乎每晚都昏睡过去。一觉醒来,我的作业已经完成,但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交上去的。我还会在剧烈的颤抖中醒来,感觉世界要撕裂了(临床上称为 "末日来临感"),感觉自己要发作了,这些都是酒精戒断患者的常见症状。戒酒?我才 21 岁,我到底在极力逃避什么?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,答案很简单:我自己。

有很多次,我知道自己需要改变。在一屋子忧心忡忡的朋友面前,抓着打不开的酒瓶把手。在前男友告诉我他不相信同性恋,变性人不应该存在后,我在车里泣不成声。翻开一页页空空如也的笔记本,上面只有泪痕。我唯一能找到的安宁就是逃到布莱克斯堡周围的阿巴拉契亚小径,在那里,我最担心的是找到回到小径头的路,以及安全地爬下岩壁。如果我还想继续徒步旅行,就不能喝酒。
这条山路教会我尊重自己的身体--因为如果我不尊重自己的身体,就很难继续前行。
在山路上,如果没有手机服务,我就无法听到厌恶变性人的评论,而我的身体能带我俯瞰令人难以置信的美景,这让我的性别焦虑症得到了缓解。在我独自远足和背包旅行的过程中,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既不像女人,也不像男人。我介于两者之间,和周围的自然世界一样自由。我无法融入性别社会。在山路上,我对每一张要求我勾选男性或女性的表格都犹豫不决。每走进一间浴室,我都会考虑再三。我害怕用代词介绍自己;我担心自己不够 "他们/她们"(they/them),不够 "她/她"(she/her)(straight)。我想尖叫。于是我就这么做了--我走到小路上(在确认周围没人后)尖叫。我想上厕所就上厕所,想挖洞就挖洞,感觉自己是个粗犷的户外人。
在户外,我会忘记一切形式、卫生间和代词,只为活着而欣喜。我可以做我自己。我是谁一个诗人,一个恶棍,一个人类。山不在乎我也不在乎
一天下午,当我坐在龙牙山山顶看日落时,我突然意识到,如果我不开始接受自己,我可能会在认识真正的自己之前就死去。于是,我离开了这段关系。在那之前,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。我知道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
毕业后,我找到了一份工作,这份工作也给我带来了和恋爱时一样的束缚感。在那里工作的头六个月,我就遭到了某人的性骚扰,而且我从未觉得自己可以谈论任何有关我的性别或性取向的事情。
我又回到了壁橱里,只不过这一次,我又多了一份恐惧,那就是我被困在了一个老男人们认为很有吸引力--而且经常让我知道--的同性女性身体里。
这不是我第一次遭遇性骚扰。16 岁那年,我在一家餐厅工作的两年里,几乎每晚都会遭到性骚扰,餐厅里三四十岁的男人会抓住我的臀部,把我束缚起来让别人亲吻。我以为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会有所不同。我错了。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老板,他告诉我:这种事情还会发生。 于是我辞职了。我开始敲定我最大的逃离计划:徒步穿越阿巴拉契亚步道。
与此同时,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越野跑中。我一直喜欢探险跑。上高中时,放学后跑上三四个小时,意味着我可以探索高山,闯入玉米地,沿着废弃的火车顶跑。在我的身体经常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被用来对付我的时候,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
就这样,在新工作遭遇性骚扰三个月后,我发现自己站在了 50 公里赛的起跑线上。

这一次,通过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超级马拉松俱乐部,跑步给我带来了一个由新朋友组成的支持系统,也给我带来了一如既往的自由。我告诉自己,我是在用跑步来准备参加 AT。然而,跑步成了我的新嗜好。我已经训练过度。
在超马过程中,我能感觉到我的膝盖内侧韧带像橡皮筋一样绷得紧紧的。我感到非常疼痛。但我不想让它停下来。我跑得更卖力了。我很生气。我的每一脚都踩在地上,我感到沮丧,尽管我有资格胜任这份工作,尽管我已经从一段有毒的关系中解脱出来,尽管我开始接受自己的非二元身份--但这并不重要。面对那些未经我同意就将我的身体性化的人,我仍然无能为力。我甚至对自己是个女人都没有共鸣,而其他人却在利用我的女性特征来对付我。我不想待在自己的身体里。我在身体里无能为力。除了我可能对它造成的伤害之外,我无能为力,在那些时刻,我觉得我的身体活该。我觉得我活该
赛后,我几乎无法行走。回到家后,我无法进食、喝水或排便。我(真的)爬到了床上。当我醒来时,我的左腿抬不起来,臀部灼痛难忍。我本该在两个月内徒步走完阿巴拉契亚步道。我做了什么?

一夜之间,我从未来的徒步旅行者和超级马拉松运动员变成了受伤、失业、住在朋友沙发上的流浪汉。哎呀。生活总是让我惊讶,它能如此迅速地改变我的自我认知。我决定将我的上瘾性格转化为强烈的自我保健。这一次,我全身心地投入到物理治疗中。理疗师说的任何话都是我的个人戒律。在我痴迷跑步的过程中,我的臀部已经错位,现在我要努力让它们恢复水平。理疗师要求我平躺,减少走路,每天做三次以上的拉伸运动。起初,这似乎很容易做到--但如果试着坚持两个多月,就会变得很困难。有很多天,我都很难不对自己的身体--总的来说,对自己--再次感到沮丧。我把自己搞得一团糟。这都是我的错,我甚至可能无法踏上我计划了一年的旅程,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场长达六小时的比赛。
每当这些念头开始悄然袭来,我就意识到担心未来毫无意义,因为我还没到那一步。我让自己感受到内疚和遗憾,然后温和地告诉自己是时候向前看了。我会吃点零食(通常我只是饿了)、喝点水,然后把挫败感转化为弹吉他、画水彩画或写诗,让自己回到当下。当消极情绪渗透进来时,我发现最好先找一些事情来帮助我的身体,然后再做一些事情来帮助我的心灵。用莎士比亚的话说,没有什么东西是好的或坏的,是思想让它变成这样的。 在一次独自徒步旅行中,我曾向一位徒步旅行者请教,他说:"有时,当事情真的很艰难时,你只需要坐下来呼吸一分钟。在恢复的那两个月里,我做了很多呼吸。

我每天都做伸展运动,尽力庆祝每一个小小的胜利。我抱着这样的心态:每天,我的身体都在一点一点地康复。你允许自己头脑中出现的负面想法越多,你赋予自己的力量就越大--你可以从我在超级马拉松比赛中的思维过程中看到这一点。如果我对自己的身体和未来的目标有更多的关注,也许我就会停下来,更多地去照顾自己。消极只会滋生不幸。无论如何,这段恢复期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,让我更加乐观,更加善待自己。毕竟只有我一个人住在我的脑海里,所以我不妨把它变成一个美好的地方。
我尽力保持积极的心态,因为我取得了一些小的胜利,比如躺下时可以伸直腿,可以完全直立,可以迈开步子,可以再次行走--然后,可以再次行走一英里以上。我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深的了解和尊重。自我憎恨可能会推动我走完 32 英里,但它不会帮助我走完 2000 英里。时至今日,在 73 天的时间里,我没有错过任何一次重复的拉伸运动。我计划继续在山路上锻炼。

现在,我把 4 月 19 日的出发日期看作不仅是一次逃离,更是一次自我接纳之旅。一路上,我将为 "Venture Out 项目"筹款,这是一个非营利组织,专门为同性恋和变性人提供背包旅行服务,让其他人也能在大自然中找到与我一样的释放和力量。我希望我的自我接纳之旅能够帮助其他人迈出自己的第一步。在布莱克斯堡周围的小径上,我找到了平静,从性别社会中获得了自由。在一次超级马拉松比赛后,我找到了自我的力量和对身体的尊重。更重要的是,我在自己的皮肤上找到了一个家,并找到了时间来治愈我的心灵和身体之间的联系。如果我在准备越野赛的过程中发现了所有这些自我发现,那么我迫不及待地想在缅因州找到自己。
Recent articles
Other categories
You might also like
Built for the Outdoors
see ALL PRODUCTS在Instagram上关注我们
不仅仅是一家户外用品公司